第二次青藏科考之藏西風化剝蝕考察
滿江紅 千仞高原
千仞高原,穿蒼穹,雄鷹峻霸。旖旎處,羚羊疾飛,寒山蕭殺。秋意微涼念烈日,暮色云天影西霞。蘭草漾、湖光粼驚鳥,風飛沙。
牧人苒,度晴夏。山巒絕,盡足下。馬背馳遼闊,嘯逢仰恰。長路崎嶇向阿里,一曲一措皆羅加。瀚途間,風霜沒乾坤,雪域颯。

千仞高原 絕頂一覽眾山小
引言 青藏高原剝蝕風化作用的重要性
在大陸剝蝕風化過程中,地表物質(zhì)從陸地向湖泊/海洋的遷移,調(diào)節(jié)全球營養(yǎng)鹽循環(huán)和生命演替,最重要的是硅酸鹽巖風化通過消耗大氣CO2調(diào)控長時間尺度的碳循環(huán)和氣候變化,從而深刻影響著地球的宜居性(Walker et al., 1981;Berner et al., 1983;Hilton and West, 2020;Tang et al., 2021)。
作為新生代以來全球最重要的碰撞造山帶,青藏高原地區(qū)新生代以來構(gòu)造活動極為頻繁,一直以來是研究構(gòu)造運動、大陸剝蝕風化與氣候變化之間科學(xué)關(guān)系的關(guān)鍵和熱點區(qū)域。Galy和France-Lanord(2001)指出發(fā)源于青藏高原南緣的河流(Ganges-Brahmaputra River)相比全球平均值而言,具有更高的侵蝕風化速率,有力地支持了Raymo和Ruddiman(1992)提出的青藏高原隆升引起風化剝蝕加速進而導(dǎo)致的新生代變冷的假說。此后,West et al.(2005)研究認為,物理侵蝕達到臨界值后,受限于化學(xué)風化動力學(xué)限制,化學(xué)風化不再隨物理侵蝕升高而增加,即搬運限制vs.風化限制。然而,最近的研究卻發(fā)現(xiàn),化學(xué)風化在極端高剝蝕區(qū)似乎確實隨著物理剝蝕的增強而持續(xù)增加(Larsen et al., 2014),這對經(jīng)典風化動力學(xué)提出了新的挑戰(zhàn)。因此,有必要在極端高剝蝕條件下直接探索物理侵蝕與化學(xué)風化之間的關(guān)系,證實/證偽以上假說。這也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(xué)考察研究所設(shè)置專題“高原風化剝蝕歷史及氣候環(huán)境效應(yīng)”(2019QZKK0707)的核心任務(wù)之一。在第二次青藏科考的契機下,全面適時開啟高原周邊和內(nèi)部剝蝕風化的基礎(chǔ)研究,2021年我們進軍的目的地號稱“天上阿里”的藏西無人區(qū)。
一、天上阿里 中緯極地
阿里地區(qū)位于中國西南邊陲、西藏自治區(qū)西部、青藏高原北部。其行政區(qū)橫跨羌塘高原腹地、西喜馬拉雅及岡底斯等地質(zhì)構(gòu)造區(qū),地處青藏高原北部-羌塘高原核心地帶。東起唐古拉山脈以西的雜美山,與那曲地區(qū)相連;西及西南部抵喜瑪拉雅山西段,與印度、尼泊爾及克什米爾地區(qū)毗鄰;南連岡底斯山中段,臨日喀則地區(qū)仲巴縣、薩嘎縣;北倚昆侖山脈南麓,與中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(qū)相鄰。其介于東經(jīng)78°24′--86°20′,北緯29°41′--35°52′之間,東西跨度742千米,南北跨度688千米,面積約34.5萬平方公里。境內(nèi)分布有多條高大山脈,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,號稱“世界屋脊之屋脊”,因此被稱為天上阿里。

阿里地區(qū)地理位置圖
阿里地區(qū)地處青藏高原腹地,地貌上具有明顯的高原特色,為青藏高原之冠,稱之為青藏高原之高原。總體上西部眾山匯集、地勢高亢,現(xiàn)代冰川雪被發(fā)育;東部羌塘高原區(qū),地形相對開闊平坦,山脈起伏不大,山間湖盆廣布。縱觀阿里全區(qū),西北部受昆侖緯向構(gòu)造帶和喀喇昆侖弧形構(gòu)造帶的控制,聳立起了與構(gòu)造形跡同向的呈弧形展布的昆侖山脈與喀喇昆侖山脈,其間形成了一系列弧形斷陷谷地,西南部及中部大面積的羌塘高原區(qū),受北東向、北西向兩組構(gòu)造的穿插切割,山脈不連續(xù),起伏大,山間形成了眾多高海拔湖盆。削高填低的剝蝕風化作用,塑造出了千差萬別的地貌形態(tài)。
阿里地區(qū)基本屬于高原季風氣候,夏季一般為青藏高壓控制,印度洋季風可沿河谷進入,造成降水,但其影響遠不及高原東部。冬春主要受西風環(huán)流影響,造成大風和強降溫。在地理位置、海拔高度、太陽輻射、地形和大氣環(huán)流的綜合影響下,全區(qū)形成了不同氣候區(qū),即南部普蘭、札達一帶為高原溫帶季風半干旱氣候,中部噶爾和日、革吉、改則的南部以及措勤為高原亞寒帶季風干旱氣候,北部羌塘高原為寒帶季風干旱氣候,具有高寒缺氧、氣壓低、多雷暴、多冰雹、降水少、蒸發(fā)量大、日照時間長、大風盛行的特點。氣候條件十分惡劣,被稱之為中緯極地。
在藍色星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條件下,阿里地區(qū)物理剝蝕極其強烈,其作用包括凍融冰劈、行星風劈、重力坍塌等,沿219、317、318國道到處可見雜亂的物理剝蝕堆積物。然而,本區(qū)平均海拔在4663 m左右,飛鳥絕跡,是西藏三大無人區(qū)之一,有關(guān)風化、剝蝕的研究幾近空白。本次科考選擇阿里地區(qū)作為科考目的地之一,考察在極端高物理剝蝕條件下,化學(xué)風化對高原隆升和氣候變化的響應(yīng),或為解決上述物理剝蝕與化學(xué)風化之間關(guān)系的爭議提供新的視角和證據(jù)。

青藏高原風化剝蝕科學(xué)考察隊
二、地熱廣布
阿里地區(qū)蘊藏著豐富的地熱能,有獅泉河—雅魯藏布江地熱帶,昆侖山—可可西里地熱帶,岡底斯山—念青唐古拉山地熱帶。阿里地熱顯示具有數(shù)量多,形式多樣,水溫高和活動強度大的特點。地熱活動類型有溫泉(25℃~60℃)、熱泉(60℃~95℃)、沸泉(>95℃)、噴氣孔,冒氣地面,熱水湖等。阿里現(xiàn)已查明28處地熱泉,其他熱水活動區(qū)21處,阿里地區(qū)所轄7個縣,每個縣都有地熱泉分布,且呈現(xiàn)出一定的規(guī)律,地熱泉的密集程度從北往南由疏到密,泉水溫度也由低到高(廖光宇等,2005)。在碳中和的背景下,合理利用地熱資源將變的尤具前景。
溫度從來都被認為是化學(xué)風化的重要控制要素之一,這也是地質(zhì)空調(diào)假說的核心論據(jù)。然而,以往對化學(xué)風化的研究中,溫度要素都只能從眾多因素中間接獲取。地熱為研究化學(xué)風化過程中,溫度的作用提供了絕無僅有的直接視角。因此,直接在阿里無人區(qū)地熱廣布處開展溫度梯度對化學(xué)風化的影響及化學(xué)風化對溫度的響應(yīng)將引領(lǐng)新的風化研究潮流。部分成果可以對太陽系內(nèi)行星風化研究起到借鑒作用。
三 科考收獲
本次科考的路線極其艱辛,藏西羌塘無人區(qū)相間幾百公里才能碰到居民聚居點,早晨需要摸黑起床趕路,否則晚上趕不到下一個居民點是非常危險的事情。藏區(qū)的旅店提供的早餐都要等到9點才供應(yīng)(時差~1.5小時),這時候外面也沒有餐廳開門,因此我們只能帶一些餅干、干糧行路。中午在牧區(qū)考察連信號都沒有,更不用提午飯。偶爾遇到牧民,會提供一些純天然酥油茶,就著面包會是特別幸福的一天。
有艱苦卓越付出就有如涌泉般豐厚的回報,本次科考到目前為止,已經(jīng)采集到了一批特別珍貴的樣品,包括海拔6800米的雪山雪、受地下高壓作用超過110度的沸泉水、地熱區(qū)受梯度溫度控制的化學(xué)風化(蝕變)樣品、無人區(qū)的自然風化剝蝕樣品等。這些樣品在現(xiàn)代大型儀器的測量下,將向科研工作者傾訴阿里地區(qū)風化剝蝕史、碳中史及其效應(yīng)等科學(xué)問題的答案。這些樣品來之不易,歡迎有新的科學(xué)想法、想的科學(xué)問題的老師、同學(xué)們共同研究這些樣品。
致謝:藏區(qū)牧民提供非金錢所能丈量之幫助;感謝前赴后繼的科考隊員們不畏艱險,用青春熱血筑起研究自然的最前線,一厘一寸拓展人類的認知邊界,尤其感謝第一次青藏科考的前輩科學(xué)家的求索精神,指引著我們前行。感謝孫有斌所長提供的寶貴修改建議對本文的提升。

青藏高原科考前輩
參考文獻:
廖光宇 等,青藏高原古近紀-新近紀地層分區(qū)與序列及其對隆升的響應(yīng)[J]. 中國科學(xué):地球科學(xué), 2010(12):1632-1654.
Berner, R.A. (1993) Paleozoic atmospheric CO2: Importance of solar radiation and plant evolution. Science 261, 68-70.
Galy, A. and France-Lanord, C. (1999) Weathering processes in the Ganges-Brahmaputra basin and the riverine alkalinity budget. Chemical Geology 159, 31-60.
Hilton, R.G. and West, A.J. (2020) Mountains, erosion and the carbon cycle. Nature Reviews Earth & Environment 1, 284-299.
Larsen, I.J., Almond, P.C., Eger, A., Stone, J.O., Montgomery, D.R. and Malcolm, B. (2014) Rapid soil production and weathering in the southern Alps, New Zealand. Science 343, 637-640.
Raymo, M.E. and Ruddiman, W.F. (1992) Tectonic forcing of late Cenozoic climate. Nature 359, 117-122.
Tang, M., Chu, X., Hao, J. and Shen, B. (2021) Orogenic quiescence in Earth’s middle age. Science 371, 728-731.
Walker, J.C.G., Hays, P.B. and Kasting, J.F. (1981) A negative feedback mechanism for the long-term stabilization of Earth's surface temperature.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: Oceans 86, 9776-9782.
West, A.J., Galy, A. and Bickle, M. (2005) Tectonic and climatic controls on silicate weathering.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35, 211-228.
科考見聞賞析

藏羚羊

陷入沼澤的防水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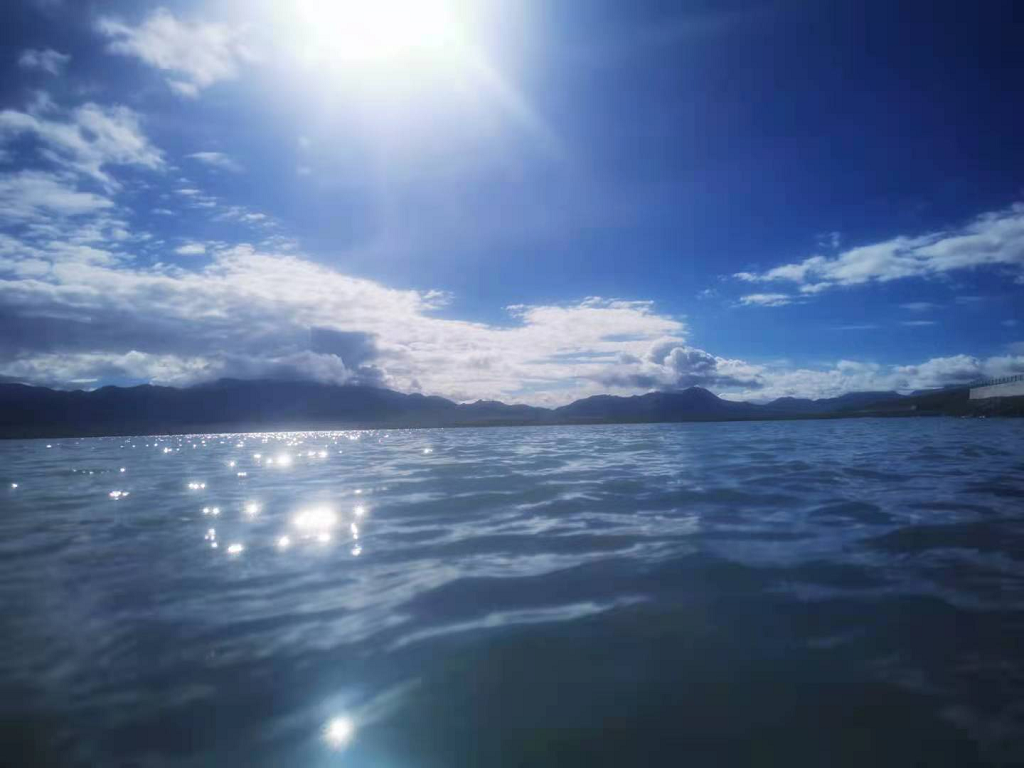
達繞措


